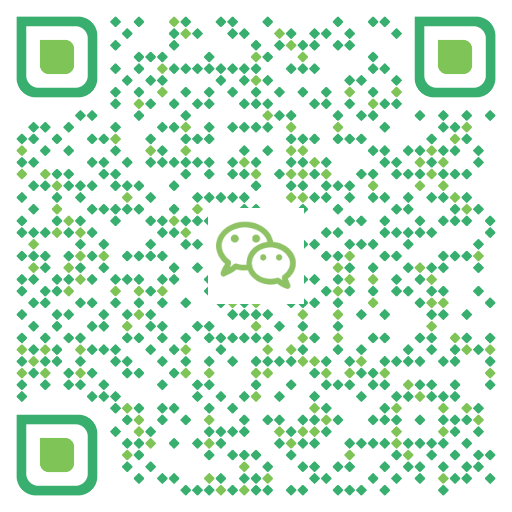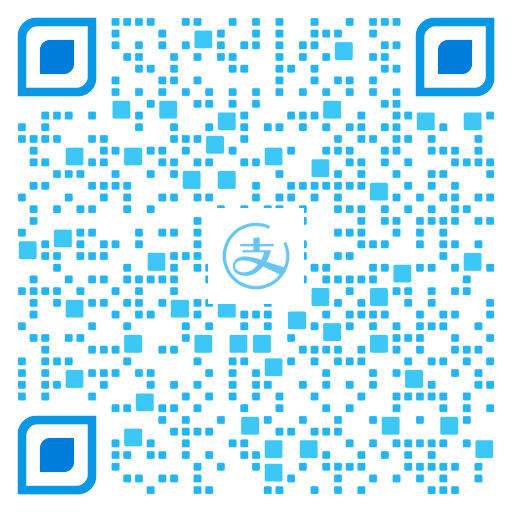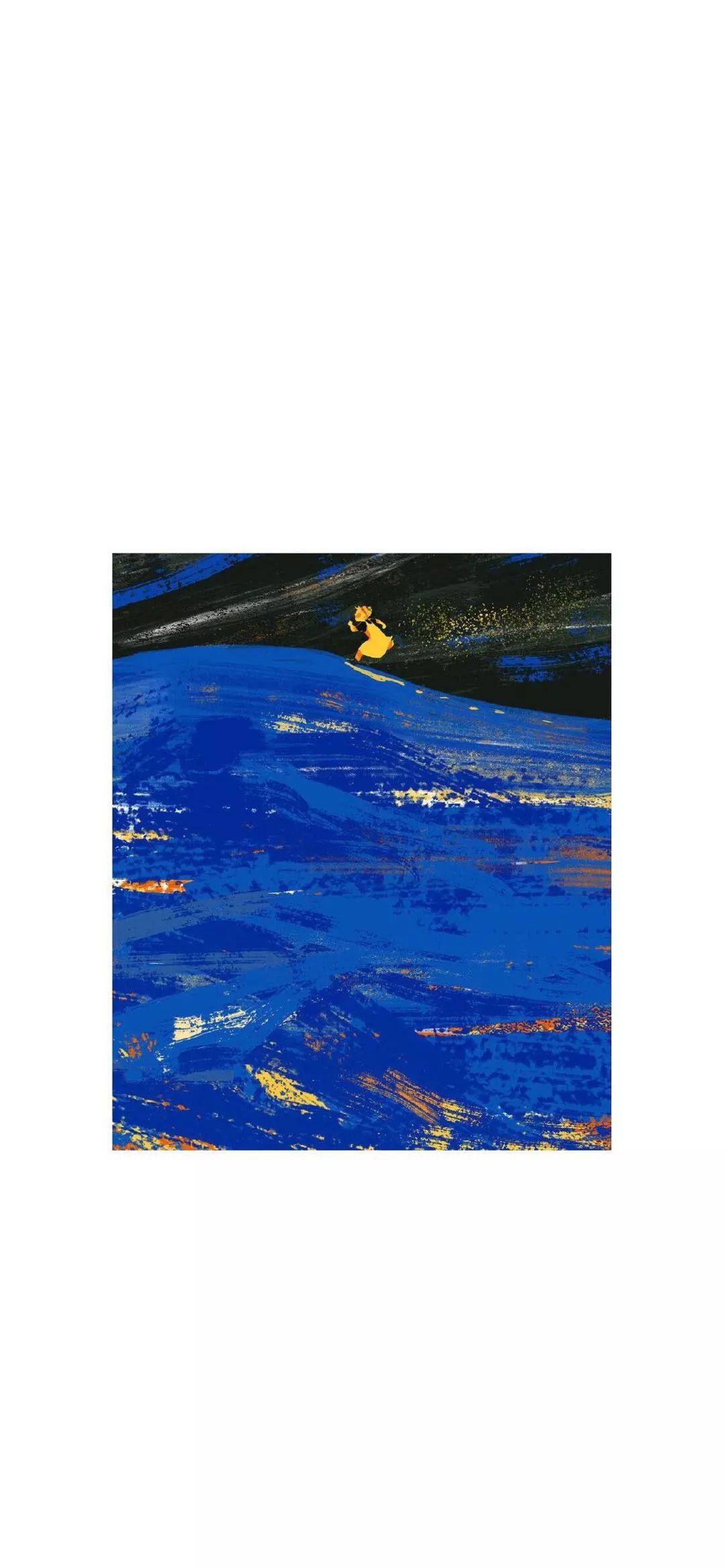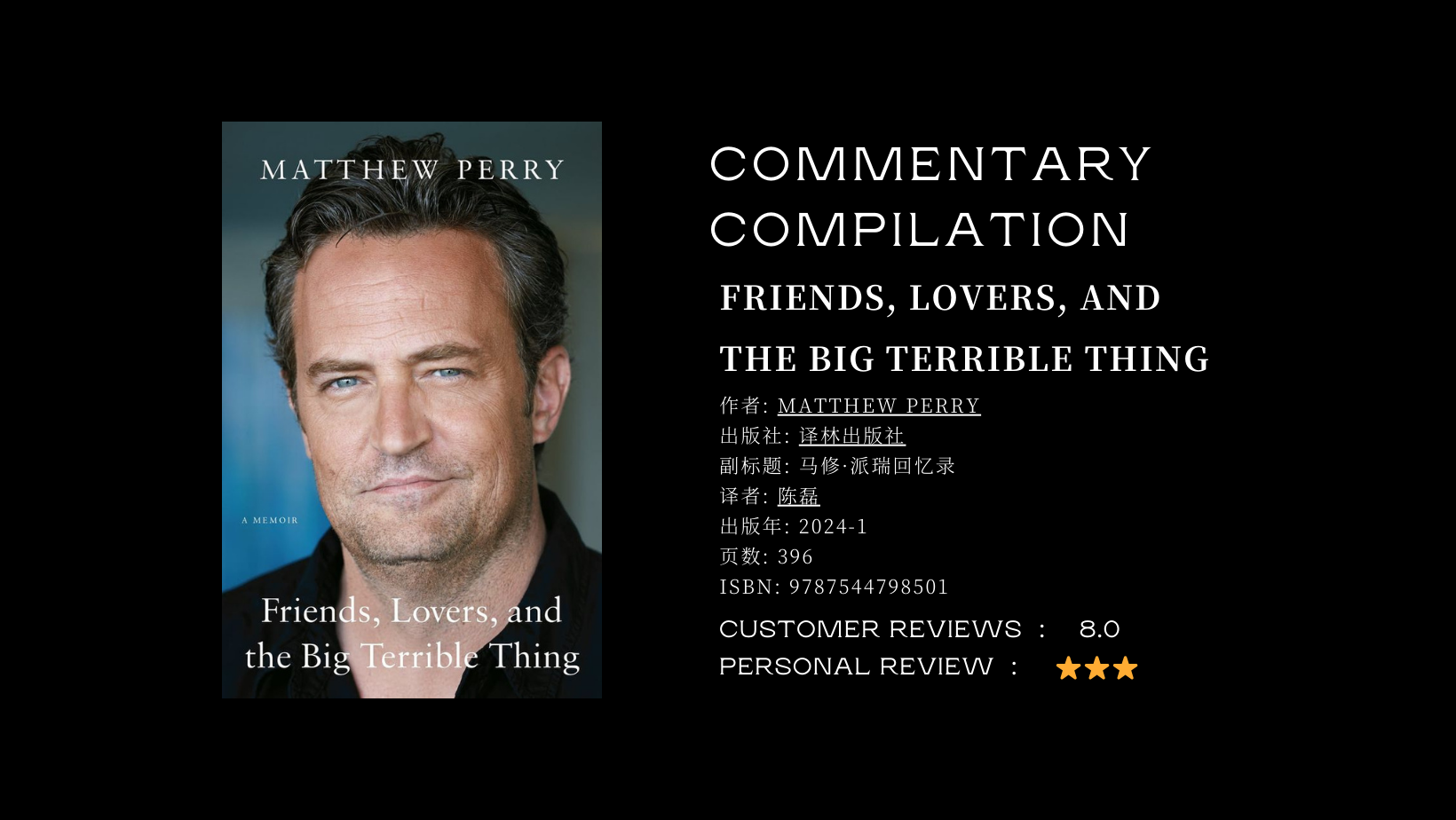“脑子今天晚上病了。”
[!quote] “好吧……”她说,仰面躺着,很惬意,“我喜欢好的食物,像牛排和脆炸薯泥那样的东西。我喜欢好看的书和杂志,还有乘火车的那些夜晚和飞机上的那些时光。”她停住了。“当然,没有按照喜欢程度排序。如果要按顺序排的话我得想一想。但我喜欢坐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你会有一切都无所谓的感觉。”她把腿搁在他的脚踝上,“我喜欢晚上睡晚点,第二天早上赖在床上不起来。我希望我们能经常那样,而不是偶尔一次。我还喜欢做爱,喜欢在不经意时被爱抚。我喜欢看电影,过后和朋友一起喝喝啤酒。我喜欢交朋友。我非常喜欢简妮斯·亨德里克斯。我希望每周至少去跳一次舞。我希望总有漂亮的衣服穿,希望在孩子们需要时,不用等就可以给他们买衣服。劳里现在就需要一套过复活节的衣服。我也想给加里买一套小西服或类似的衣服。他长大了。我希望你也有一套新西服。其实你比他更需要一套新西服。我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住房,不再每年或每隔一年就搬一次家。这是最大的心愿了。”她说,“我希望我们俩能过一种诚实的生活,不用去担心钱和账单之类的东西。你睡着了。”
——雷蒙德·卡佛《学生的妻子》
(一)
每次阅读卡佛,即便只是再短不过的一段,抑或一首诗(当然我很久没读过了)都会感受到一股刺痛。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唤起了共鸣。
可能是角色的那种“处境”——再稀疏平常不过的生活,却无从把控,那种只能望着一切被摔得支离破碎的失控感;
可能是卡佛调用的语气——无力挣扎且毫无修饰地呈现生活本来的残酷面目(但却被人为摘去了某些东西——你知道非常重要但又说不上来的某些东西)。
直到今天,在不知所措下重又翻开,才最终将之“捕获”:或许,那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匮乏”——物质的匮乏、性的匮乏以及精神的匮乏。
这么说可能有某种“庸俗化”的倾向,可在小说中,困窘和贫穷确实构成了一堵高墙,即便身处这边的人们想要纵身一跃,也触碰不到任何可支撑他们完成翻跃的地方。
当下与以往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曾经,身处“这边”的人们无从想象身处“那边”的生活,可现如今,这堵墙虽然依旧存在,但原本的质地已然被凿空,浇筑成透明。看似身处两边的人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享受同样普照的阳光,但只有当个体接近时才发现,原本以为的其乐融融不过是一厢情愿,“乐”与“乐”之间仍有甚远之距。而原本可观可感的墙面,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触不可及。尽管无比厌恶毒鸡汤里说的那句话“校服是贫富差距的遮羞布”,但却也不能不承认其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事实”。
在极为盛行的认知中,贫穷在当今已然被“确证”为一种“原罪”,尤其在“消费”已然被史无前例地顶礼膜拜的当下。而“匮乏”,在这个时代也转变了含义,在绝对之外,相对性业已成为其更主要的所指以及诸多“痛苦”的根源。
对个体而言,在彻底失却“校园”赋予自己的“镀膜”之后,它从生活的隐脉中逐渐“浮出地表”,成为一种无时无刻都可被触碰、体认的主轴。这个过程恰若被细针刺破而渗出的鲜血,一点点晕湿了贴身的衣物,到最后留下一片无可清理的“狼藉”。
更重要的是被外在表征遮蔽的内部反应——毕竟,借由一个狭小的穿孔,被导入名为“生活”身体的“病毒”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过程中对宿主不断侵蚀。在此过程中,“器官”也在向“坏死”的终局演进,其所带来的改变甚至连本人都难以察觉。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大致勾勒一个路径(就像我刚刚已经在做的那样):
首先是时间的匮乏。
bullshit job 倾吞了你所有的时间,当然,美其名曰是给你点事情做,让你感到自己“活着”。
其次是精力。
通勤、与人沟通交流、日复一日机械化的工作事项,它们填充的不只是时间,更阻绝了个体的感知,你所能做的、所能思考的种种种种,都被框定在一个又一个“日程”之中,并被赋予面目可疑的“意义”。
忙忙碌碌一天之后,能有多少人依旧保持“好好生活”的精力呢?
再次是物质的匮乏,或许这才是整个过程最难让人忍受的部分。
“对等的报酬”、早已被“规定”的“权利”已然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承诺,或许务实地说,它不过是那根挂在驴头上的“胡萝卜”。(由此你就知道,明明具备强制执行的能力却从未强制执行的所谓的“为民者”其行为与言说的虚伪。)
当然,在此过程中,匮乏带来的痛苦如同天山童姥给三十六洞主七十二岛主下的“生死符”,需要定期服食“解药”。或者简单点说,像潮汐一般,不定涨落。
而当你用仅有的闲钱投身名为消费主义的“麻醉剂”,到头来或许会发现,这不过是延迟最差结果到来的时间。不得不说,这种反复本身倒似少年初尝自渎之乐,令人在行动时的如痴如狂与行动后的恳切自责之间辗转徘徊。
(二)
这些日子,我不断使用 AI,从 GPT 到 Gemini,甚至想方设法开了会员。
他们说 AI 时代是一个知识平权的时代。
在我连续半个月都在想方设法把三个账号的 Gemini cli 的 2.5 pro 免费额度耗完,在我日复一日地为了同一个目的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该死的 prompt 之后,我确实咂摸出了这句话的些许意涵。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越来越厌恶它对我的迎合,它的不知反思(当然可能是我用的方法不对),和那些在我看来非常不应该存在的细节疏漏。
但是,我得承认,在跟 Gemini 做了几十轮深刻探讨(既然没有继续深造,我也不妄称学术二字)之后,我发现它确实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窥探到很多未曾涉足的领域。而且说实话,每一次对一个问题深入探讨的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你错失保存硕果的良机,你可能就真的无法找回前一个半小时辛苦进行的十几轮思想交锋(惨痛的教训)。但话又说回来,我并不认为它戳破了围绕着我的茧房,后者只是被撑的更大了,在 xyz 三个轴体上都是如此。或许我也不应苛责,因为更可能是我自己将自己困缚在茧房之中,不愿脱离。
其实我想说的是,当我试图通过 AI 去探寻那些缠绕在我脑海深处的种种困惑的时候,我发现,它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好使。或许,我所触及的都是一些确实难以解决的症结问题,也因此,它总会随着我的思路一次次倒向一个又一个死结。
可是,当我不断看到它的坚定,坚定地觉得一切还是会被解决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羡慕。(实际情况是,唯有第一次与这种坚定的相遇是给我带来了由衷的欣慰,越往后,我对这种刻板的乐观主义越觉得厌烦。)
换句话说,我一边服膺于自由意志,相信自主思考能为个体带来独有的“光辉”;另一边又渴望被植入“思想钢印”,希望自己真的能够永远“敢于去相信”。
可我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那一切我所希冀的改变最终恰巧略过了自己的一生,我又怎么不会感到一种“欺骗”——换言之,我们真正成为“承前启后”的一代——未能分享改革的余温,只能在种种不甘中继续作为“换取未来美好”的“柴薪”。
现在,我终于看清,自己其实从来都没有那么“高尚”。我之所以在这里那里呼唤,不过是希望自己能在自己的往后余生能早一天“享受”到这一切。而如今,我却怀疑这份“享受”不过是一种异想天开,是一种可笑亦可悲的一厢情愿。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不去做收缩,不去向那些自己无比厌恶的媚俗以换取物质的行为看齐?
(三)
[!quote] 有好多年,我和我妻子都拥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如果我们辛勤工作,尽量做对事情,就会心想事成。按照这种信念,尽量营造出一种生活,这样并不算很糟糕。辛勤工作,目标,好的意愿,忠诚,我们相信这些美德迟早会得到奖赏。我们梦想获得奖赏的那天。但是最终,我们意识到辛勤工作、心怀梦想还不够。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爱荷华市,要么是不久以后在萨克拉门多,梦想开始幻灭。那段时间来了又去,当时,我和我妻子视为神圣的一切,或者认为值得尊重的每种精神价值,都分崩离析了。我们遇到了可怕的事,这种事,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出现在别人家。我们无法彻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侵蚀,我们无力阻止。
直到如今,我依然不断在想,如果那一切都没有发生该多好,就像卡佛写的:“当时夏天的夜晚总是星光灿烂”,“朋友们,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生活。”直到如今,我依然在骨子里这么认为。可“我们从惯常感知的保护壳中被推了出来,仿佛我们突然身处自身的外部,飘浮在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世界上。”
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吧!
我们无一例外地被“生活”捶的鼻青脸肿、面目全非(如果有差异,那或许也只是程度而已)。“我们就迷失在了那个世界。我们甚至无法希望从中找到我们的路。”
当然,我不能美化自己,说什么当时自己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但至少,在校园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暂时放弃功利这个选项(说实话,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这样做了),有纯粹追求热爱的这种可能。可后来,它们都被一一斫断了,而且这个过程比起其他人所要经受的,来得更毫无预兆、不由分说。
而当那一切“结束”,我们再一次重逢的时候,也比以往更多地陷入沉默。因为,加诸个体的苦闷,无法述说,无从述说,“又能说什么呢?我们都还太麻木了。”我们都接受了这一切也习惯了这一切。
就好像,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言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索性放弃。即便我们本就知悉,自己所付出的那些时间原本是为了让自己坚持述说下去。可到头来,记忆还是成为了所有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就好像那是自己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唯有将之封存才能继续将“生活”维持下去。
或许也正是因为“勘破”——更确切地说是朦朦胧胧中觉知(直到如今才在不断的确证下将之置换为新的“真理”——但你又怎么知道当时的自己不是拿着手里珍贵的“生活”去替换了失去尊严的“活着”呢?)“前进”是必须且刻不容缓的(虽然更多是被迫的)。我们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成人,开始意识到,是时候为自己的“未来”打起算盘了。
只是,当时的我(或许直到如今),都没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一切都到了这番境地:曾经一度渴望“在天上”,但真正被抛掷其中,却发现,自己压根适应不了这名为“失重”的新的恒常。
当然,你可能觉得我矫情,毕竟,“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失败和希望幻灭都司空见惯。我们多数人或早或晚,都会怀疑自己哪儿做得不好,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按照我们计划的进行。”为什么只有你不能接受?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往前”走?
我为自己预设了太多反对,太多“劝诫”,到后来,它们有的被说出,有的被藏在话头后面,作为某种心照不宣的、期盼我能自己觉察的“注脚”。
如此一来,失衡后的无法调整被归因于个体,创伤只能被隐匿于虚假的繁忙,记忆不再被调取,就像一切从未存在,都是某种虚设的臆想——我一直不理解,这一切怎么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至于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奉为圭臬。
直到如今,我才一点点意识到,其实,那些曾被强行忘却的,如果你不去将它们一点点挖掘出来,去表露,去述说,去还原它们本来的面貌,那这些往日的幻影就永远不会如你所愿的那样离你而去。虽然现下里彼此相安无事,你也终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与它们撞个满怀。
是以,即便可能被目为沉陷在往昔之中无法自拔的“亡魂”,我依然愿意坚信“打捞”的价值。因为,我已明白,我的“义务是看见眼前的事物(即使它在他身体里),并说出我看见了什么”;因为,书写于我,就是找回主导权,“当我写下来,生活就像一本日记本一样容易放下。”
当然,我也曾一度怀疑,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我正在写的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但我发现,除了写作,我再难寻得其他解释并理解自己人生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爱德华·路易的表述:
[!quote]
我不怕重复自己,因为我的所写所述并不遵从文学要求,而是出于必需,出于紧急,因为水深火热。
即使,人们对我说文学决不应自我重复,而我只想书写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反复写,直至它能够让人一窥其真相片段,一个洞接一个洞地挖,直至隐藏于后的东西开始渗出。
人们对我说文学决不应像感觉的堆砌,而我写作只为让身体无法表达的感觉喷涌而出。
人们对我说文学决不应像政治宣言,而我磨快我的每个句子就像磨快刀刃。
我坚持那个笨拙的信念:想知道自己是谁,就需要不断去进行这样的拷问和探寻。
我相信,如果没有彻底说清那段时间对我乃至对我们的意义,如果没有彻底深入这段无论是个体意义上还是整体意义上的“历史”的核心,它就仍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刻刺痛你我的内心——就像老王对哈姆雷特做的那样。
可以说,自那以后,这份执念(虽然并非一直作为主轴)成为所有思考和追问的原点,它(部分地——现在我终于能够正视这一点)造成了我的支离破碎,也让我试着去重新把自己拼为整全。
只是,我想我仍然需要某种努力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而如今,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具备这一切。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否挨到解明“真相”的那一天。
我多希望自己也能像奥斯特那样:“没有因为它们看起来如此荒谬、难以实现就抛弃我所有的理想……”即使“看见世界正渐渐变成荒野,听见不断迫近的雷声,那也会毁灭我们;能感受到百万人的苦难,但是,当我抬头望向天穹,我想一切都会好的,这残酷也会终结……”
但对于这一切是否真的会变好,当我追问的越多,试图了解的越多,我越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世界就是如此向你我一一呈现:像是溺水者,在一次次几乎要寻到“支点”的时候,却发现,那个“支点”本身也在加速沉陷。
为了存活下去,自己只能避开每一次长者的“谆谆教诲”,只能对所谓的“关心”惨然一笑。
成都不无决绝地对我说:一切都是钱,只是这话出自他口,我才一直不置可否。但现实却是:在一个所有人都以此为标的物和判断尺度的社会,你怎能不去想:妄图超脱不过是一种徒劳的尝试?
因为,事情确实如同它们口中述说的那样:你必须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才能换取构筑新尺度的“资本”。所以,在“被同化”和“超越”都不可能的现在,我选择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跟“死人”说话,“他们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也是唯一能理解我的人。”
这也解释了所有人的不解:路一直在那里,为什么你一直选择视而不见,还为由此带来的痛苦叫嚷?
因为无法相互理解,所以他们最终都会拿出那句让我尤为厌恶的陈词滥调:“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但我总在怀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走到如今这个地步,是经由“自主”选择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所谓“条条大道”归根结底不过是一条路的“虚像”,那所谓的“自主”是否本身就是虚妄)。
我怀疑的是,说我们曾经相信的这一切都是错的人,他们究竟是以何种面目何种立场做出判断;
我怀疑的是,如果这一切都是错的,那为什么我们自始至终都对“正确的”(反道德的一切)东西三缄其口;
我怀疑的是,他们难道不是因为知悉自己本身并没有表现得那么确定,才会如此强调?
当然,这也是一种解释,对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宁可转向可笑的“影子政府”和所谓的“深层法则”也不愿意再去相信他们原本奉行的一切其实并没有问题。
到头来,簇拥着要打倒这一切的“我们”,终归只是以同样可笑的姿态,坚定不移地让自己从一极倒向了另一极。
处在这样的世界之中,我们怎能想象,自己仍有“美好的未来”?
(四)关于“疼痛”的“拼贴画”
[!quote] “我还记得那句话,”她眼睛看向窗外,停顿片刻,然后接着说,“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最后一句是——”我说,“抱着那样的希望,我继续活着。”
——保罗·奥斯特《幻影书》
去年春天,在通勤的路上,我第一次与卡佛邂逅。
记不清有多少次,到站换乘的间隙,不得不强行让自己从那种难以自拔的悲哀中抽离出来。
那时,跟其他许许多多的时刻一样,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糟透了,我就那么无能为力地望着自己的生活,就像卡佛在诗中写的那样:
[!quote] 我的朋友完蛋了,没戏了,他也知道。这儿是干吗?没人能帮助他们吗?大家非得眼睁睁看着他们垮掉?这让我们都感到沮丧。得有人马上出来救救他们,立刻从他们手里买下一切,在此生活的每点痕迹,别再让这种丢脸事再持续下去,得有人做点什么。我伸手去摸钱包,这才明白:我谁都帮不了。
我望着朋友和自己的生活,希望有人能帮帮我,然后我想自己就能抽出时间和精力去帮帮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自己能够摆脱“谁也帮不了”的境地来以此帮帮自己。
但这份期待最终沦为空想,而我也悄无声息地逃离。为了从又一次“落败”中寻获某种“救赎”,到头来,自己能够找到的方法跟所有那些作家笔下的失意者一样没有新意。生平第一次,我下单了一提烧酒。
当它最终抵达,当我一杯又一杯将之吞咽下肚,希望它多少能起点效应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无法释怀。
就像奥斯特说的,虽然,“酒精担负着遗忘的机能,但责任在于世界。”而我们又要“如何谴责世界”?“它所规定的人生令我们周围的人除了尝试遗忘外——使用酒精,通过酒精——没有其他选择。遗忘或死亡,或遗忘并死亡。遗忘或死亡,或遗忘并因竭力遗忘而死亡。”(至少,直到如今,我仍是这么相信的)
即便将自己灌醉,还是会无力地发现:“你哭不出来。你无法像人们通常那样伤心。”“于是,你的身体崩溃了,替你伤心。”(至少,直到如今,我依然如此)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此后还将一次又一次)(通过阅读)清晰的意识到“如果我想要拯救自己的人生,那么我必须走到离毁灭它只有一步之遥。”
对我而言,“再没什么能让我意外,因为我已无任何期待,再没什么是暴力,因为我们管暴力不叫暴力,我们管它叫生活。”
后来,我继续任凭自己的灵魂“随风飘荡”,因为没有书写,没能书写(部分是客观限制,部分也是主观的放弃),它只能那样,带着情绪、零碎消散的思想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一起,保持一种未命名的状态(就像液体缺乏容器的固定而不断流动着)。直到我开始阅读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作品,我终于为自己的状态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语境”,就像她说的那样:
[!quote] 我的身份不是难民,但与难民一样,我也无处可回。……我只能说,我从如今看来已非常遥远的过去出发,尚未抵达目的地。
或许,这是“僭越”,是某种不知好歹的类比,可我确实还没能找到另外一种更恰切的指称方式。
不得不承认,身处此地,呼吸带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滞涩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能轻而易举地看出自己与所处环境之间清晰分明的“界限”,继而意识到本应由自己保留的“空间”也在逐渐被后者侵蚀,就像一滴不怀好意的油渍一点点渗透进来,你却拿它毫无办法。
或许,最难让你接受的是,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你所爱和说爱你的人都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反过来,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充当着你所厌恶的这一切的“帮凶”——打着爱的名义。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像其他所有人那样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就像我无法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去努力,无法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融入软件背后的生态,无法为了合群而去合群。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选择了这一切(或许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只是我不愿意承认),但我相信一点,即是:对于我这样的“流亡者”而言,唯有文字与语言能让我们“回去”——当我们说到“回去”,“它的意思似乎不只是从冲击中缓过来、恢复意识、回到生活,还有回到自身,仿佛有一片空间和一个人,他在空间里漫步,寻找着回家的路。”
是啊,“流亡”,我敢说,此生我再没见过如此贴切自己一直以来状态的能指。我的心,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它被放逐在一个任谁也找不到的地方,飘啊飘啊,反而飞向更远的方向。但我或许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怨怼,不应该像哥哥说的那样——做一个习惯性扫兴的人。因为,至少现在,还有他愿意时不时会去看看它,如果碰上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把它捂热一些,然后点点头,告诉它它走偏了方向(虽然更多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但我想自己也应该感激,至少他的出现,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些许好的影响)。
说实话,自从走出家门,进入这滩巨大的令我窒息的死水之后,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我们面对着一个庞大且充满敌意的世界,却要想方设法融入其中;为什么我们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得以保全,“就甘愿付出了比生命本身还要高昂的代价”,毕竟,在“这场挣扎中幸存下来的只有保卫生命的本能,而生命本身早已流失,只剩下‘生命’个空名。”
有谁能说自己不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囚徒?即便高贵如贵胄君侯。
有谁能说,在这个时代,自己不是压抑的,扭曲的?
有谁能说自己的心没有生病呢?
作为“流亡者”,“我环顾四周,就像一名遭遇海难后刚被冲上海岸的水手。”继而发现,“我住在一个不属于我的国家里的不属于我的城市里的不属于我的公寓里,周围是剥落的墙皮和发霉的味道。我手中的遥控器还能用,但我的内部控制装置已经没电了:不管按多少下,我都动不起来。我在想,过去发生的事是什么时候找到时间发生的。”我像一名哭丧人,“我为每一个人的痛苦而痛哭,唯独我自己的痛苦没有声音。”
乌格雷西奇说:“回到我们出走的土地意味着死亡,留在我们来到的土地意味着失败。于是,离开的情景在我们的梦里无尽地重复,离开的那一刻是我们唯一的胜利时刻。”在途中,我们“既过早地衰老,又永远长不大——两者是同时的。”
可吊诡的是,我却确信自己看到那些从“群”中寻得归属感的人们“内心的分裂,他们的愤怒,被压抑住的抗议”即使他们从来都不曾表露。
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是一样的,“我们全都遭受过某种侵犯”。
当然,我也要承认,“每一次伤害似乎受到了真实、讽刺或怪异的处理——但总归是处理了。有些人的伤口恢复得很好,有些人不好——但也算是恢复了。就连疤痕都在消退。”就好像“人人都有去处,有人发挥特长,有人勉力而为。”
或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正是因为“生活发给有些人的牌比其他人好一些”,所以,即便“死者与失踪者有待清点,许多恶徒依然逍遥法外,许多瓦砾有待清理,许多地雷有待拆除”,对他们而言,尘埃似乎已经落定,生活也能继续下去了。毕竟,像他们这类人,永远都会有立足之地,对他们而言,“就连不幸也是需要管理的:缺乏管理的不幸只是失败而已。”
“他们能迅速找准自身定位,永远盯着关键机遇,像九命猫一样顽强,他们工作努力,善于沟通,忠诚,嘴严,宽容,友好,而且善于应对高压环境。……他们会在申请书中加上挑战是我的动力、我的最终目标是尽善尽美一类的话,以及当代自我、当代融合化、后殖民主义、市场化、招聘策略、敏感性训练和联结一类的术语。”
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优秀”的能力,
[!quote] 走在路上的他们忘记了:将他们抛射到地表的灵活性、活动性和流动性恰恰留下了一群无名的、底层的奴隶。在灰色的死水里,人们到处都在生产着富豪们渴望的商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会在垃圾桶里找吃的,纵酒无度,产下无家可住的孩子,孩子又产下更多无家可住的孩子。
他们不再希望那些“过去”被重新提起,也就要求那些仍然未能走出的人放弃自己发声的权利。
对于乌格雷西奇们来说,
[!quote] 这种对直面现实的绝对拒斥是随着战争而来的。在战争期间,现实以轻薄,甚至比马里索尔和卡桑德拉的台词还要轻薄的字幕的形式溜进了家庭。那就是它被容许的全部空间。肥皂剧是你打在恐惧上面,将恐惧冲掉的泡沫,每天要打两次,最好是在朋友的陪伴下。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拒绝则源自未被彻底清算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机械进化论和盲目乐观主义的混合,它作为一种你我他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获悉的“观念”,在个体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上被一次又一次蓄意重复,最终内化为一种看似“天生”的意识形态,当一个人不具备这些东西,他就会从“我们”中被除名。
或许,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深深陷在属于自己的不幸之中。所以,几乎每个人都不愿发生在彼此身上的“对大灾难感同身受。至少不会长期感同身受。”
我想,造成这种漠然氛围的原因并不那么复杂:既然,对于身处此地的个体,苦难是难以更改的存在状态,那就只好接受它是与生俱来的常态;在日常生活中压倒性的“常态”叙事包裹下,个体无法想象另外一种存在状态,无法去寻求另一种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匮乏”,所有对现有叙事的突破都会被目为“异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很难不承认下面这个事实,即是“这个国家确实除了受害者就是加害者。受害者和加害者会定期调换位置。”
在这种“恒常”中,“解脱是没有的;有的只有遗忘。而遗忘来自我们的大脑中都有的神奇小橡皮。我们每个人都拖着自己的壁橱,每个壁橱都有自己的骷髅头。骷髅头迟早会滚下来,不过会披着伪装,以一种让我们舒服的形式滚下来”。
因此,人们心照不宣地坚信:总有一天,正义(包括美好的明天)会来到的。(虽然在我看来,它就像戈多,如果只是等待,那就永远都是一厢情愿。)
人们坚信着:等待是拥有意义的,即使在血痂褪去之后留下的累累疤痕仍然那样刺目,缝合处的隐痛依旧。
在这样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的坚信中,疼痛是证明这一切多少有些虚幻缥缈的“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那奔涌于你我血管之中,通过太阳穴表露出来的疼痛。那单调地重击着你我的疼痛。那失聪的、麻木的、盲目的、突然令我们感到不安,表明有些事情错得离谱的疼痛。”
(五)
[!quote] “脑子想离开这儿去到雪上,想跟一群毛发蓬松、龇着牙的动物一起跑在月亮下,跑过雪地,不留爪印或足迹,什么都不留下。脑子今天晚上病了。”
——雷蒙德·卡佛《冬日失眠》
那天晚上,母亲骑车送我到小区门口。
临别的那一刻,终于忍不住,我告诉她我对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一切的真实想法: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路边的一条羸弱不堪的野狗,任谁路过,看不顺眼都可以踢上一脚。”
说完这句话,我看到她脸上讶异的神色,仅仅是那个瞬间,我再一次确信,她永远也理解不了我的感受,就像我生命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
没等到她矢口否认,我便像个逃兵一样,快步向前走去。
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只是对这世间的一切感到心理与生理性的恶心。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生命而非生活,已然被麻木感笼罩。这种状态不像游戏中那么容易,当你积累了几个“祝福”、恰到好处的“方程”就能引发“蝶变”。相反,当你积聚越多,你会发现,那种任你如何挣扎也无法脱离的窒息依旧如影随形。
当你被日复一日的选稿出稿改稿以及诸如此类的bullshit压榨到无力——无力思考、无力书写、无力阅读,最终一点点看着自己油尽灯枯,看着自己逐渐变成最不想变成的庸碌无为并对此甘之如饴的人;与此同时,你所珍视的情绪、感知也在被渐次剥离,只为了能够让这副残躯维系最具功利性的、作为整体机器其中一个“齿轮”的价值——这也是它唯一“被认可”却从未获得认可的价值。
我想,对此产生反感和疑惑都是可预期的举动。
换言之,仅仅为了所谓的“活着”,你就必须舍弃其余的一切,这过程就像亲手跟墨菲斯托签订契约出卖自己的灵魂(当然,你不得不承认很多飘忽于世的行尸走肉压根不具备这东西),然后在不打麻醉的情况下(我忘了,身体和精神上的疲乏与倦怠本就是最好的麻醉)任凭它们把你最为珍视的一切(在我看来那即是意义)一点点从身体上剥离。
都到了这个地步,让人不得不去想,如此这般换来的继续“活着”到底是否真实?你怎么知道自己最终换来的不是一具苟延残喘的躯壳?
而要想尽量让它“保持完整”,为了从这种状态中将自己“拯救”,你依然不得不去完成一次更为痛苦的自我剥离——将身心都血肉模糊地撕裂开来,成为两半:一半为了存在,一半为了忘却(但可悲的是,忘却也是为了能够继续“存在”,两者其实是互斥的,但为了能够维系自己的运转就得不断让彼此的铰链纽结缠绕得越深)。
为了完整,先要残缺,为了这样“活着”,你却先要一遍又一遍杀死自己(将心从体内剥离)。
如果说这还不够吊诡,那么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竟觉得如此这般地将自己碎裂为两半(让我说的更明确一些:一半在工作中疯狂泯灭人性,另一半在喘息的间歇疯狂寻回那些曾被泯灭的人性)是保全自己“唯一”的选择。看着自己从起初的拒斥到排异再到最后的麻木,以至于最终接受自己唯有维系这种精神分裂才不至于伤毁的事实,我时不时会想:自己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承认,“我没有资源,内部的、外部的都没有”,但我怀疑,这难道就是自己不得不妥协的理由?
我也承认,在整个被“捏塑”的过程中,“我是脆弱的。任何人都可以把我捡起来,让我仰面朝天,对我为所欲为,给我留下淤青与伤痕。……我已经失去了人格。我戴上了用来抵御侵害的面具,面具已经和我的脸融为一体,深入了我的身体。我不再是自己了。”但在那些无法入眠的夜里,我还是不住会想,难道自己的往后余生就只能这样度过?
在这种状态下,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快疯了。我走着走着路,突然就不得不停下来收拾碎片,我自己的碎片。我的胳膊,我的腿,啪!还有我发了疯的脑袋。你都不知道,找到你们我有多高兴。不管怎么样吧,我把碎片粘好,又维持了一阵。我以为彻底粘好了,但又碎了。于是,我再次捡起碎片,像拼图一样把自己拼起来,直到下一次……”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所剩无几的“自我”只能在阒寂的夜里,在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最后的梦境之中踽踽独行。
对我们而言,“失败者心理已经扎根在我们的心脏,弱化了那里的肌肉。”
即便我想,像所有那些到最后有力地反驳这一切的家伙一样,说什么“即便如此,你依然能够感受到一种,你可以称之为执念抑或其他什么的东西,它在阻止你放弃挣扎——哪怕一丝一毫也好”(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我发现,自己也做不到。
现在的我只是讨厌被这样的人审视——那些“每每遇到需要正视的问题,却偏把目光移向别处。一旦问题被指出,又抱怨‘难道只有这件事重要吗’‘为什么你只说负面的话’‘难道不能谈些积极的话题吗’”的人;那些强行将“希望”这个词据为己有,觉得“只有克服绝望、闷头往前冲”,才有资格谈及它们的人;那些“漫无目的,只知道要拼命向前”的人。
说到底,我厌恶这样的“希望”,我也不认为这种“希望”能够指引向某种“未来”。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在“希望”这个能指的掩饰下一次又一次“逃避,只是借此在自己的绝望上盖了一层遮羞布。一旦有风吹来,绝望就会再次翻到明面上。”
当然,我知道,“频繁地经历相同的绝望,会消磨人的感知能力”;我也知道,他们早已认定“一切终归徒劳”,甚至连尝试的念头都没有。于是,只剩遗憾与无意义的责怪,而对所谓“和谐”的执念,反倒成了导致不和谐的根源。于是,他们只能“止步于此”,在一次次停滞和失败中,人心也逐渐变得粗糙。
但我还是疑惑,应该做的,能够做的,难道除了对近在咫尺的彼此的煎熬、苦痛视而不见之外就再也没有了吗?如果这就是他们强行据为己有并刻入基因的“希望”——只是为了让“人们在跌倒后重新爬起来,在‘明天会有所不同’的期待中继续忍受痛苦”;并因此有恃无恐地挖苦质疑者:“真麻烦!”“只有你辛苦吗?”“这点事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甚至习惯性地嘲讽别人活该。
那我觉得,这样的“希望”反倒最应该被翦除。
即便在此种“暴政”面前,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逐渐输掉的战斗”。但“努力挣扎时造成的伤痕,以及附著其上的硬茧,为了战胜人生的拉力而形成的肌肉,让我们得以继续坚持下去。”
就像朴相映写到的:
即使是悽惨的痛苦,有时也会成为希望的碎片。我想要如此相信,所以写下这篇文章。
为了不失去这个信念,我也会继续写下去。
【1】(荷兰)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著,何静芝译:《无条件投降博物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
【2】(荷兰)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著,姜昊骞译:《疼痛部》,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
【3】(法)爱德华·路易著,赵一凡译:《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
【4】(法)爱德华·路易著,赵一凡译:《谁杀了我的父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
【5】(美)保罗·奥斯特著,btr 译:《冬日笔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
【6】(美)保罗·奥斯特著,btr 译:《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7】(美)保罗·奥斯特著,孔亚雷译:《幻影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8】(美)雷蒙德·卡佛著,孙仲旭译:《火》,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8】(美)雷蒙德·卡佛著,小二译:《不管谁睡了这张床》,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24年。
【9】(韩)吴赞镐著,玉鳍译:《是我的错吗?:直击韩国12起恶性社会事件》,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10】(韩)朴相映著,郭宸瑋译:《想成为一次元》,台北:漫遊者文化,2023年。